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自由,有用无用之辩也扰攘不休,何谓自由而无用?
毕业之后,社交场合,总能碰上这样的寒暄:“你一看就是复旦的。”当然是套近乎,可猜个八九不离十,多少令人称奇。
复旦的学生究竟有何种共通的气质,以至众生之中,无所遁形?最常见的回答是:自由而无用的灵魂。
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自由,有用无用之辩也扰攘不休,何谓自由而无用?

创业的朋友说得好:“不是很想招复旦的学生,眼高手低。”学文的同学更妙,他们搬出了里尔克的诗句,“将生命演出,不再顾旁人的喝彩。”借以表达对切近功利和琐碎现实的有意疏离。
孰是孰非,或未可知。能确定的是,眼见的自由与无用,都在复旦的人与物之间。
2005年入校,正值复旦的百岁生日。既是华诞,总要大张旗鼓地庆祝。新生身在班级、社团,少不了填坑的任务。但在专业课的课堂上,却不止一位老师直言不讳:“有这些时间,不如多读点书。”政令可以批评,小我理当彰显,对历尽规训的学生而言,在最表浅的切入点上,忽然就嗅到自由的清新。

通识教育的试点,也是从2005年开始的。当时,所谓通识教育,不过是文理专业混编进同一寝室。可一年之后,粗疏的通识课程,连同自主招生的方案、实践,都已初具规模。光是选课表,就能仔细研读两三天,这种自由度,怕是值得珍惜。
对初入校园的年轻人,大学无异于人文景观的集成,教授也是不可不追的明星。很多年以后,鲜少有人再记得每堂课上讲授的知识点,但特定场景中的人情与风貌,却历久难忘。
我相信,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,复旦,是骆玉明老师讲台上的绿茶和餐巾纸,是王德峰老师课堂里的袅袅香烟,是张汝伦老师偶尔的拍案而起,也是陆谷孙老师的舌灿莲花妙语翩跹。当然,在夕阳的余晖里邂逅贾植芳先生,或者躬临朱维铮先生的最后一课,更是遥远的幸运,回想起来,都恍如梦寐。
学生不肖,夫子文章未及分毫,但先生之风,却常在心间。自由而无用的印记或许也在于,虽然不言不语,叫人难忘记。

我在新闻学院念了研究生,师从李良荣教授。前阵子网上有个说法:“去年的《同桌的你》,今年的《左耳》,感觉离现实生活都太遥远。没有抽烟,没有堕胎,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情仇。我的求学路上,陪伴我的只有两个男人。一个温柔了时光,一个惊艳了岁月。我至今都能清晰地忆起他们,一个叫郭庆光,一个叫李良荣。”
学友诚不我欺。李老师不仅以精绝的厨艺震慑麾下群“雄”,更有一句知名的劝诫:“少谈些政治,多谈些恋爱”。
其实,李老师的学术趣味是极其严肃的,但处世的宽厚仁和,都在这句话里。按我浅陋的理解,他是想说,爱情和政治,本质上,都是自由的故事。而自由的初衷,应该是个体的幸福。

当然,自由与试错是双生子。毕业前后,复旦经历了黄山、投毒的风波。近来,关于崔永元和转基因的争论也甚嚣尘上。是是非非,再正常不过。高校难逃舆论的漩涡、政治的逻辑,象牙塔或者学术共同体的理想常提常新,本身也意味着现实的龃龉从未远离。
置身其间,人与人的分歧,在所难免。护短和苛责的校友,可能都不愿承认,复旦再亲切,再声名远播,说到底只是尘世间的一部分。而自由的所在,按理也容得下异见和多样性。

早先日月光华bbs的开机页面有一句话:为谁盛放花满路,旦复旦兮心如故。这应该是怀缅青春时光的意思。在复旦度过最好的年华,理当追念。
每次在公开场合,全场起立,校歌的前奏响起,也常常心头一热。学术独立思想自由,政罗教网无羁绊。踏足校园,这是模糊的憧憬。待到离开,无论是确信,还是愈加怀疑,也都会将这句箴言牢记心间。
不是每个学生都会主动走进校史馆,但那些日常,诸如相辉堂、子彬院、光草、3108,或者闷热的宿舍楼、漫步的操场马路、周边的街摊食肆,都已成为深挚的烙印,不期然地闪现在脑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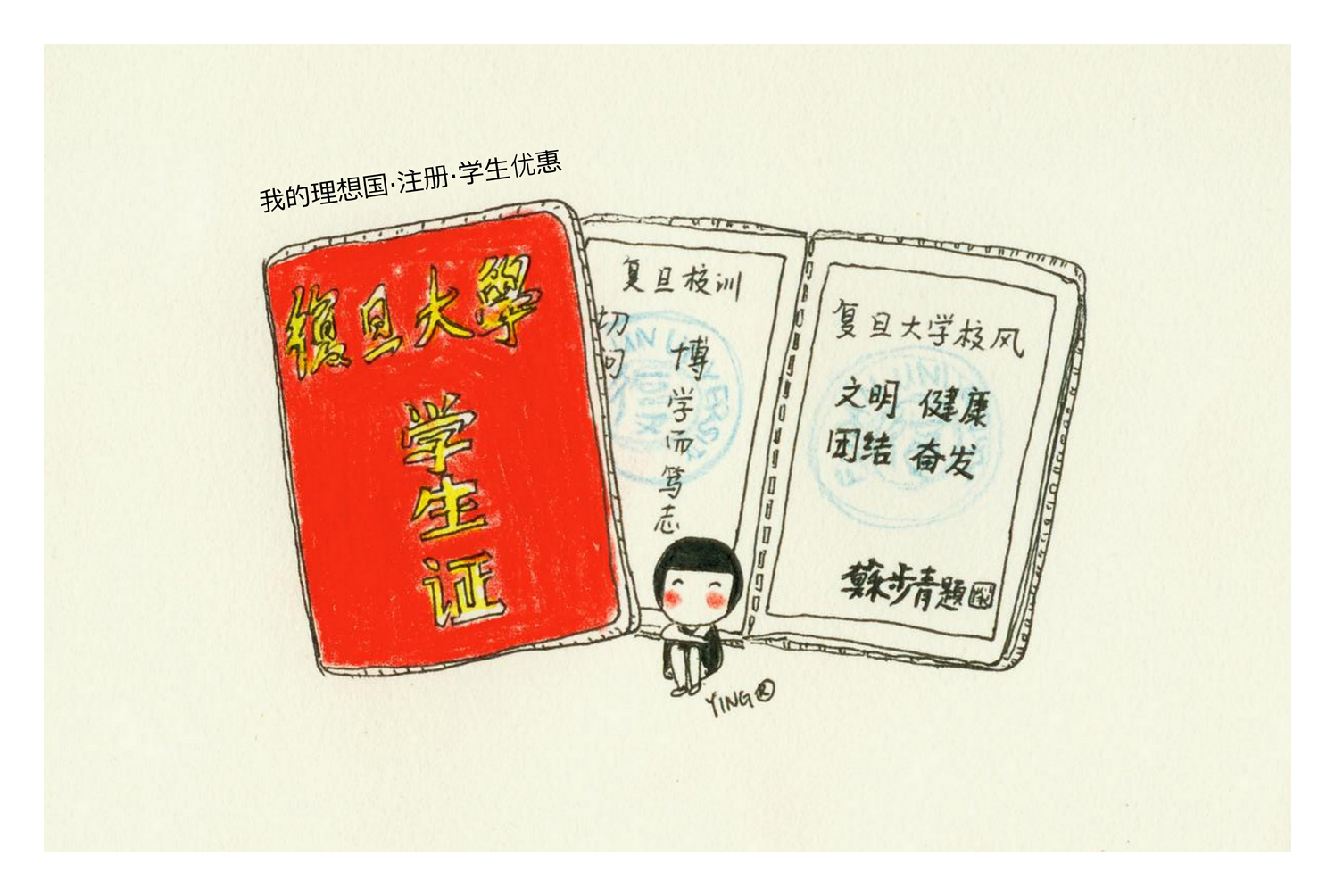
以前写过:“之于这所学校,我们只是沧海一粟,而它的烙印,却长相陪伴我们,去到更多更远的地方。”这句话,杨玉良校长在去年的毕业典礼上引用了。
他未必会知道的,是一个普通毕业生的衷心谢忱。我们不可能熟稔复旦悠长历史中的一草一木,但亲见的自由,包括自由的是,自由的非,都已深嵌肌理、摄入心神,陪伴此后的人生长路。
在这个意义上,每个人的复旦,每个复旦人,都是一个关于自由的故事。
谨以此文献给母校110岁生日。
